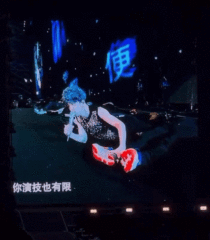韩国n号房间事件始末 韩国n号房是有多恶心涉及的明星有哪些?
韩国n号房间事件始末
N号房案件,是指通过社交平台Telegram建立多个秘密聊天房间,将被威胁的女性(包括未成年人)作为性奴役的对象,并在房间内共享非法拍摄的性视频和照片的案件。
2020年3月22日,韩国警方已对涉案的共犯13人进行立案,并拘捕了为首的“博士”赵某。3月23日,赵博士身份公开,此人名叫赵主彬同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彻查“N号房”事件,要求警方调查聊天群所有会员。3月25日,犯罪嫌疑人赵主彬被移送检方。3月30日,据韩媒,主犯之一李某为争取轻判而向法官提出了悔过书4月13日,赵主彬被送上法庭,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网络性犯罪专项调查组以违反《儿童青少年性保护法》等嫌疑对赵主彬提出拘留起诉。4月16日,韩国法院透露,赵主彬团伙将从4月29日开始受审。4月17日上午,韩国警方将赵主彬的共犯姜勋送交检方,并将其公开示众;姜勋当场连声道歉。5月18日,韩国警方将文亨旭送交检方,并将其公开示众。8月27日,共犯南庆邑初审认罪,预计9月与赵主彬对质;11月2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赵主彬进行一审宣判,判处其40年有期徒刑。2021年4月8日,韩国“N号房”创建人文炯旭一审获刑34年;
2021年6月1日,韩国N号房主犯赵主彬二审被判42年;7月8日,韩国N号房共犯一审判处其17年有期徒刑。10月14日上午,韩国最高法院对“N号房”主犯赵博士(本名赵主彬)进行终审宣判,判处其42年有期徒刑。赵主彬一审获刑45年,二审获减刑,改判42年。[32]2021年11月11日,文亨旭终审获刑34年,姜勋终审获刑15年。
韩国n号房是有多恶心涉及的明星有哪些?
其实在国外娱乐圈早就被曝出过很多规则等事件,尤其是那些台前光鲜靓丽的女明星,背后的生活更是我们看不见的凄惨,近10余年来月近几十位韩女星离奇身亡。
2005年5月22日,曾经和宋慧乔一起拍摄策划的当红女星李恩珠,突然在家中身亡,年仅25岁。
事后,警方调查公布结果是她本人因为是抑郁症而身亡,但是在当时李恩珠留下来的遗书这样写着“我很想工作,但现在觉得现在过的日子是非人的日子……",另外,李恩珠房间里还留下一个记事本,上面记录着自从她当上演员后的一些感受,基本上都是感觉生活很累、心里很困惑,厌恶人世,自尊心都丢光了,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等。
后来据李恩珠生前好友爆料称李恩珠步入娱乐圈后,便经常被高管“欺负”以各种理由带回家消遣,遭名流玩弄。
自从李恩珠之后,就陆续有国外女星身亡事件发生,2年后,郑多彬在男友处上吊身亡,剧情跟李恩珠的相差无几。3年后,“国民天后”崔真实也身亡事件也是轰动一时,因为除了她本人身亡后,她的亲弟弟、前夫也上吊身亡,最后就连崔真实的经纪人都身亡,然而这件事直至今天也没有解释得了真相。
而最骇人听闻的恐怕还要数09年身亡的张紫妍,而其前经纪人公开了生前她留下的200多页的遗书,记录着其生前被经纪公司老板逼迫的种种记录,比如说一次侍奉5人、一天最高层接客不止10人、在酒里下刺激性迷药、以及被某大佬带出去外接客等等,还有好友爆料张紫妍去世前遭受侵犯太多无法生育的消息。
其中涉及的名单中有数位政商大佬、记者、导演、男明星等,从种种爆料来看,成为了韩圈的而一个惊天八卦,而张紫妍并非简单死于抑郁。
然而哪怕是遗书和数位证人出面作证,张紫妍身亡案经历3次翻案依旧以证据不足为由,无疾而终,这才是最令人后怕的事情。
风光的背后,是看不见的规则:
国外娱乐圈表面风光无限,新人一波接着一波,依旧有不少的年轻女子投身于演艺圈做“练习生”等,然而不少还签订了高额的违约金合同,说句难听的,与其说是合约,不如说是“卖身契”。
韩媒还曾匿名对韩圈女艺人做过一份调查,结果显示70%的女艺人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规则。
早前成龙也透露自己只有百年过后才敢曝光自己生前经历过的黑幕事件。此外杨幂曾在采访中自曝当初出演《红楼梦》自己本来已被定角色为薛宝钗,后来却被临时换掉,后来才知道顶替的女演员跟制片人关系不浅。
虽然是邻国发生的恶性事件,但实施者的隐秘残忍、围观者的漠然抱臂,显然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再次刷新了对人性的想象力。
而在人们反复的讨论与谴责中,更隐含着一个潜在的恐惧:如此让人作呕的事情,或许只是这个时代的冰山一角。
性暴力作为人类古老的病症,贯穿历史。
西洋古语有云:“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诚然是不易之论。然而现代历史学也会告诉我们,即便是相同的恶意,每个时代都会有各自的呈现方式。
万物都位处复杂的联结之中。就像我们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才能知道自己的性格,恶的品性也是在社会结构中才能成立。
看起来是类似的暴行,更有可能是唯独这个时代才能孕育的恶之花。
“N号房”事件令人震惊的原因既在于手法的罪恶,也在于旁观者的反映:26万的房间参与,以及韩国男性对这件事的普遍同情。
在最新的动态中,不乏有韩国女性诉说自己因为与男朋友在这件事的观点不同而被迫分手,或是有匿名男性拼命为自己的参与辩护。
许多人认为,“N号房”虽然是犯罪,但围观者并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承担高额的成本。
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主张顺顺当当、天经地义。
面对如此理直气壮的自我辩护,固然有个体人性的卑劣,但群体性的护短,则暗示着社会的病理。
回顾韩国近些年来的各类性别议题,韩国的男性与女性之间都会存在难以逾越的认知鸿沟,更关键的是,双方都觉得自己才是基础伦理的维护者。
在基础伦理的认识问题上出现分裂,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最深刻的官能症。
许多韩国女性抱怨,在谈论性别议题时自己的男朋友似乎还活在中世纪。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
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韩国作为现代化的承受者,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吞下了许多名词: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快速地出现在韩国人的笔头上,并成为金科玉律,人们大体不会认为这些原理是错的。
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一颗优良的螺丝,背后必然是发达的冶金、铸造能力的支持;这些看起来炫目的伦理,本身也有着生长与成立的环境。
伦理不是在脑子里规定出来的,实践伦理需要的是社会惯习的支持,最复杂的社会规范也往往来自于最普通的生活当中。
人们在一个小动作、一个小眼神中就能完成对事物对错的判断,深入人心的伦理本来就是在洒扫应对、请客吃饭中才能看得见的。
一旦伦理抽离出社会,降临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却得不到有效转化,那么伦理很快就会转化为教条,而教条就意味着争吵与无效。
对于韩国而言,不同的现代价值,在各个领域的转化速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韩国会看到一个高度现代的商业市场、政法系统,不那么现代的人际交往、管理模式,以及非常传统的家庭关系。
不同的社会领域存在着不同的惯习,而不同的惯习就会导出不同的伦理判断。
对于每一个现代韩国人而言,他们身上会同时打上许多个时代的烙印,他们身上会同时成立着数种彼此冲突的价值观。
就比如说平等这个价值观,在政法领域行得通,几乎已经是天经地义,不然朴槿惠与崔顺实不会引起全国性的愤慨,人们对于政治性特权的容忍度非常低。
文在寅政权的法务部长曹国,人们都知道这个人有能力、可以改革司法系统,但是高官身份连带的教育特权是韩国人政治伦理的红线,所以也一定要把他拉下马。
但这种“平等”观念,到了家庭领域就会哑火。
看韩剧比较多的读者,恐怕都会对韩国家庭的“老父亲”印象深刻,老父亲常常可以对自己的妻子与子女颐指气使,妻子与子女虽然可以在口头上揶揄、调侃自己的父亲,有些老父亲也会卖弄自己的“妻管严”人设,但在重大问题上享有话语权的只有家父一个人。
韩国直到2008年才废除民法上的户主制度。
在此之前,韩国的财产法与家庭法呈现着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分裂。
在合同法、侵权法这类财产法上,民法的主体是自然人与拟制人格的法人,民法是从一个个独立、平等、有自尊的个体出发去规定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方式;
而在家庭法上,韩国的户主制度却只认可家父作为户主的权利,其他人均作为附庸列在家父户籍之下,进出户籍都需要家父的许可。
换言之,家庭法是以“家”而不是以“人”来把握民法主体的。
一边把人当人,一边不把人当人,即便现行韩国民法已经统合了这种内在分裂,社会惯习上的伦理调整也很困难。这种斑驳、矛盾的伦理布局,会引发许多新的问题。
在旧有的社会,社会整体浸润在同一、渐变的惯习中时,不论男性女性都能理解各自的定位,“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与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是统合的。
然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必然是急速与裂变的,大量的新伦理、新价值会不断涌入并重塑这个社会。
在现代化的指挥棒下,男性与女性被迅速从家庭中抽出、整合进国家的号召。
相比于原有的社会,男性与女性、老人与青年,不同的社会阶层会被寄寓新的期待:我们期待女性的解放、独立;我们期待男性的参军、建国;我们期待所有国民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不单是家庭的成员。
新的期待产生的同时,旧的身份期待并不会丧失。
不想承担户主的男性被迫成为户主,希求独立的女性在职场天花板中撞得头破血流,公司老板搞不清楚自己和家长有什么区别,许多偷拍者尚不懂得隐私是社会的底线公德。
有的男性因为“户主气概”不够而受到欺凌,有的女性因为过于独立而被敌视排挤。
不同的社会时间不是平行发展的,他们会纠缠、打结,每一个结都会凝聚因冲突而积攒的怒气、愤懑与敌视。
韩国社会被一个个死结遍布,每一次前进都如同行走在布满地雷的平原。
以“Metoo”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运动,之所以受到了韩国男性的极大仇视与抵制,也是因为不同人看到的“Metoo”景象是极为不同的。
当韩国的男性与女性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时间,在不同的时间与惯习系统中采择不同的伦理标准,他们会发现:连“Metoo”到底是什么,都永远不会有共识。
“Metoo”作为外来运动,自身在韩国的普及也叠加了诸多不同社会惯习的意义:有些人将之看做同工同酬的渠道、有些人将之看做反对性骚扰的武器,也有些人打算将美国左翼最先锋的性别思想一并在韩国实践。
不论是“Metoo”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大家都生活在极为多元的惯习之中:首尔市江南区的新鲜男女轻易就能谈论的美国时髦思想,对全罗南道乡间的男女而言可能依旧十分陌生。
不分男女,由现代化开启的惯习分裂,其引发的伦理裂变,不仅蕴含着性别议题,也与经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
网络的高度私密性赋予了这种伤口与裂变激化的空间,被长期压抑的矛盾就有可能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
26万观看者,占韩国男性人口的1%。在平日里他们要被社会规训,相信“韩国是一个具有统一伦理的现代国家”这一童话(在大多数国家,这都是一个童话),谨小慎微地生活;
而一旦到了本身就缺乏社群伦理的互联网环境,处女地般的狂欢开拓不会带来新的价值,只能把旧有的症结放大与激化:他们兴高采烈地作恶与发泄,并认为这不是自己的错。
现代国家要维持成立,这种童话就常常显得必要,人们倾向于忽视或不承认这种分裂性时间与惯习的存在。
奥威尔小说里的术语“犯罪停止”,本来是说大洋国如何抹杀异端思想,其实在现代韩国也是成立的。
不管是韩国的男性还是女性,系统性反思这个国家现代化带来的伤痛都是需要代价的——反思可能导向思维革命,也可能导向退化保守。
毕竟,将旧的伦理视作珍宝而要全盘封建的人,与将新的伦理视作圣经而要全盘西化的人,在韩国都大有人在。
所以至少在目前为止,韩国的男性与女性们就只能互相指责。
男性沉溺在荒唐可笑的反向受害者意识里,女性对父权的批判也只能停留在西方理论报菜名。
没有共识的批判与变革,注定会喧闹与缺乏行动力。
韩国1980年代以来在政法领域推进的转型正义,才刚刚进入深水区。
打倒全斗焕那样的独裁者、实现和平民主固然难度重重,而在细部打倒每个人心目中的全斗焕,实现韩国人与韩国人真正的和解,才是真正的困难。
文在寅去年在三一运动100周年庆祝活动上曾说:所有社会不公,都是日帝思想清算不彻底的结果。
这固然能凭借“日帝”符号的绝对邪恶来对社会不公宣战,应当说是很聪明的策略。
但要让韩国人手执干戈,一面反思传统,一面反思现代化,然后在经验与共识的基础上前进,这又会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不过至少,“N号房”事件所爆发出的冷漠心态与彼此仇视的社会氛围,可以让韩国人有所痛觉,继而前进。
绝不能为暴行开脱,但也不能对背后的机理视而不见,不然这个世界只需要宗教战争便可以了。
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不是韩国自己的问题,不能撂下一句“韩国社会有病”就高高挂起。
比如说韩国的邻居日本,上野千鹤子就曾回忆说,那些参与东大抗争、反对国家暴行的男学生们,一边反抗着专制,一边又十分享受女学生在抗争前线给他们端茶倒水。
今天的日本,足够现代甚至都快赛博朋克了,却连夫妻结婚是否一定要改姓而争论不休。
再比如以博爱与自由为傲的欧洲,面对难民潮与国际冲突,却表现出了中世纪十字军一般的警惕与仇恨。
看起来整齐顺畅的现代化大潮下面,人们各种各样的惯习与时间,冲突不断。
与世界其他部分一样,现代化是韩国人的宿命,不可逆潮流而行。
但韩国的男性与女性们要如何处理心灵、社会与现代化的关系,不让暴行借缝隙而生,则或许是韩国这一代人当有所思、当有所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