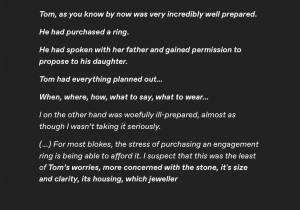胡歌谈《繁花》阿宝身世 点出剧中阿宝人生细节(2)
2、侠客岛:“时代的列车”,的确,《繁花》讲述的上世纪90年代上海,有经济的腾飞、黄河路的生机,也有许多位“阿宝”在面临人生抉择。你怎么看那个时代?
胡歌:就像阿宝说的,我们要感谢那个时代,感谢不断奋进向前、为一口气不服输的那代人。我们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可以说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但充满机遇的同时,也有迷失的风险。《繁花》讲,“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半日归零”,你会看到许多家庭经历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欢聚也有离散。王家卫导演经常在现场跟我们说“花无百日红”,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寻找或留下一些永恒的东西。比如对阿宝,最重要的就是情和义。
3、侠客岛:阿宝身上既有鲜活明亮的朝气,也有精明冷静甚至杀伐决断的一面。这种复杂性演起来困难吗?
胡歌:阿宝的多面性是时代赋予的。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那时候的上海像一杯鸡尾酒,既有质朴,也有商业时代的浮华。阿宝身上也有这种撕裂感。对我来说,这个角色确实难演,很有挑战性:有时他展露出不同面相,需要我在不同频道间切换;有时他又像搭戏台的人,邀请不同的人上台跟他一起唱戏。一开始我们手里都没有完整剧本,很难分清哪个阶段需要怎样的阿宝。但王导在我就会比较安心。
4、侠客岛:不少观众觉得上海话版的《繁花》特带劲,原著作者金宇澄就曾表示,自己努力锻造了一套保留沪语灵韵的“改良上海话”,当然,剧里的又和书里的不同。作为“上海土著”,你在剧中说上海话时有什么讲究?
胡歌:上海这座城市一直很多元,你要是想找特别“官方”的上海话,恐怕找不到。要按地域分,上海话大致可分成偏苏南、偏苏北、偏宁波和本地化这几种;要按时间分,“80后”讲的上海话是新上海话,老一辈讲的上海话,我们叫“老法”。比方说,剧里我讲“时间就是金钱”,是根据普通话直译成上海话的,但老一辈人会觉得这么说太文绉绉,他们会说“辰光就是钞票”。要是再老派一点的上海话,“钞票”要说成“铜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