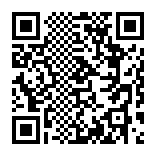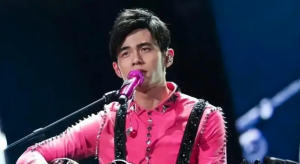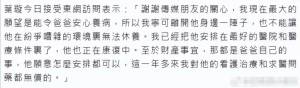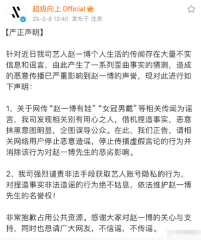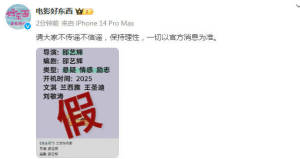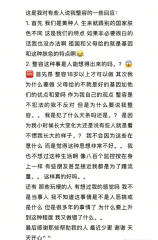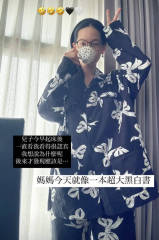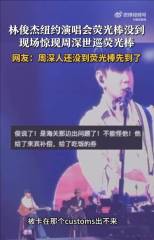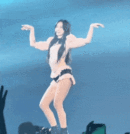《显微镜下的大明》是悬疑吗 原著小说剧情介绍(2)
帅家默最终因为私自把这笔钱用得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而获罪。作为一介布衣,帅家默根本不知道自己主张的这场官司,给徽州,甚至省里的官员带来了多少不必要的麻烦。更不会想到,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的秋后算账。
为了平息其他几个县百姓的众怒,借他胡乱花“公款”的由头,给他按了罪名,他被判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的重刑。多么明显的欲加之罪!只是,事已至此,就算帅家默想通了其中的猫腻,也为时已晚了,不是吗?
程仁清在狱中写下了《丝绢全书》原著中,程仁清和帅家默没有直接接触过。丝绢案第一版方案下来之后,作为突然要多出税赋的婺源县人,程仁清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
不同的是,作为腹中有诗书的士子,程仁清显然不只和大家一样,首先想到了毫无头绪的抗议,而是组建了抗议机构——议事局。这个组织不仅指导老百姓怎样有理有据的反对均摊人丁丝绢税,甚至逼走了县衙的主官。新上任的主官还没有到婺源,就感受到了来自那里懂得敌意。
等真的到地方了才发现,现实可不仅仅是敌意那么简单,议事处差一点就要取代官府的权威了。——如果不是他们内部有人眼红程仁清的权利,突然策划了叛变,程仁清就可以和知县平起平坐了。
程仁清这样做得到目的,最开始就只是为了帮乡亲父老抵抗均摊人丁丝绢税,以便博得一个有助于科举考试的好名声。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慢慢的就变了味道,在权利的腐蚀下,他渐渐失去了最开始的方向,最后好名声没有落着,还差点被秋后处决了——他被判处了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的斩监候。
谁让他的议事处往大了说等同于谋反呢!被关进大牢的程仁清过的并不辛苦,毕竟他所做是为本县以及其他四个县的老百姓谋福利的事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斩首示众的“斩监候”,一候就是20年。
以上内容仅中华网独家使用,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
关键词:
关闭
相关新闻
2023-02-14 11:40:18
显微镜下的大明什么年代
2023-02-17 14:59:02
显微镜下的大明故事背景
2023-02-15 14:54:27
显微镜下的大明猫现状
2023-02-16 10:40:50
显微镜下的大明哪个县
2023-02-07 13:36:31
显微镜下的大明在哪个平台播出
2023-02-07 13:30:54
显微镜下的大明是正史吗